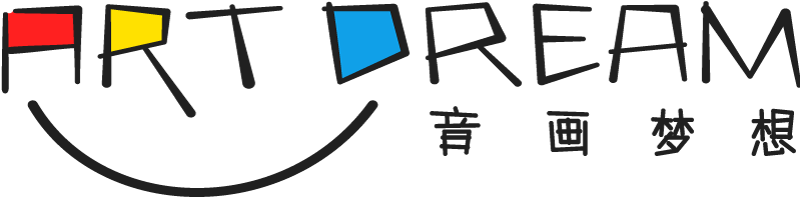张卉的艺术学习经历
我叫张卉,音画梦想的全职员工,一个自诩对艺术后知后觉的人。
小时候,承蒙母亲的引导,我倒是拥有不少短暂的艺术体验,比如,幼儿园时家里就摆着一台电子琴让我随意按压;小学一二年级就被送去学了一学期的水墨画;小学四到六年级每周末都去老师家练习硬笔字和毛笔字……但遗憾的是,这些启蒙式的艺术刺激于我来说并没有留下强烈的印象,当时习得的技法到现在早已忘却大半,反而是某些“功利性”的艺术训练经历和嘉奖让我记忆犹新。

比如,二年级时,竞选大队委需要才艺展示,这对当时是“体育生”的我是一大挑战,因此,就找了当时学声乐却得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集训了一段时间的歌唱,从简单的发声练习到识读简谱,再到选曲有感情的演唱,突击性的训练不过2周,我糊里糊涂地就以一首《海鸥》的3分钟演唱顺利通过考核,晋升大队委;
比如,四年级时,母亲期待我习得一项艺术特长以后好作为才艺展示,而我却没有很强的动机诉求。在母亲提出让我去练习民族舞来让自己更安静、更像女孩子一点,但在看了舞台上婀娜多姿的舞蹈表演后我却执意要学蹦蹦跳跳的街舞;争执不下后我提出说可以练习小提琴(原因是看动画片《名侦探柯南》中新一拉小提琴很帅),但母亲通过周边的人打听到县里目前唯一教小提琴的宋老师是个半路出家的老师,因为担心老师的专业性不足,就搁置了我的提议;作为交换,母亲提出说要不然去练习钢琴吧,正好有亲戚认识的老师是师范专业毕业的,而且也能教。我没有抗拒,抱着好奇的心态去老师家接受面试。面试时,正好赶上老师结束对一个5岁孩子的教学,老师打量了我一会儿说,虽然年纪有些大了,但我个子高,手指修长,应该是个不错的苗子。或许就是因为这个老师嘴里的“优势”让我有了些自信,觉得不好好利用自己的“先天优势”有些浪费,而且钢琴看起来也比小提琴高级,自己不亏,所以就这样一头扎进了钢琴的海洋中,一学就是4年,直到接连跳级地考完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业余钢琴水平的最高级,而我也因此成为了他人口中“速成钢琴”的“别人家的孩子”;
再比如,在高中的时候,因为自己有些识读五线谱的经验以及个子太高在女生的合唱队伍中略显突兀以外,我被委任了“指挥”这一角色。当时自己愿意接受的点不在于指挥有多好玩儿,而是觉得自己能够作为全班同学合唱节目的总把控,那种“被强需要”感觉很开心;而且,穿上黑衬衫系上银色小领带而不是穿着粉色裙装在全校师生面前亮相的感觉让当时还是个“假小子”一般的我在“主流”和“自我”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合唱比赛终了,我们班取得了年级第二的好成绩,而我也被评委老师誉为“全场最帅指挥”,那个在舞台上手捧奖杯闪闪发光的自己,也成为了我中学记忆中难以忘记的“高光时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家庭和性格因素,导致自己在与艺术打交道的过程中,自己总是那个“画画没有创造力、音乐学习缺乏乐感、情绪反应要比人家慢三拍”的笨小孩,又或许是小时候这些艺术活动目标指向性都过于明显,我自己在这一系列的艺术互动接触、练习中,更加关注自己通过“勤奋”来实现自己在技能上的进阶挑战。因此,自己会因为艺术才艺获得了其他人的“好评价”而开心,而在“如何感受艺术带来的美好”上始终没有开窍。在外部评价撤离时,我感受、学习艺术的动力也丧失了。比如,每每填写报名表时还会在特长一栏写上“钢琴”,但当他人问到自己说,你一般多久弹一次琴的时候,我却支支吾吾地找借口说,“近来太忙好久不练了”……但真实的原因,其实我内心清楚,是自己始终把艺术当成了任务而非真实的、激发热情的爱好,所以,慢慢它就败给了生而为人的懒惰天性。
再次跟艺术结缘,是因为工作上的“误打误撞”。虽然加入音画梦想不是因为艺术,而是因为自己对于线下教育的好奇,但在音画梦想这个自带艺术属性的平台上,我因为2次偶发性的契机对艺术以及背后更深层次的美育教育、人文精神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而这也让我感受到,艺术于我将不再是任务,而是可以投入热情、坚持一生的爱好了。
第一次是发生在2018年年中。自己在正式入职一年半后,我对自己过去偏重项目管理技法而轻谈教育、艺术的工作经历不太满意,一方面是源于对项目的执行结果有心无力,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做进一步优化;另一方面是我在疲于用那一个“钢琴速成”故事去激励大学生后深深的自我消耗。“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推荐这个?我真的从艺术中获取滋养了嘛?”在不断的自我反问中,我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案。而那种状态又被自己认为是对工作的不负责任,我在心里暗自嘀咕,如果艺术教育带给我的就是这些,那么我有什么理由把这样的“好东西”推荐给更多的人?但我又不希望轻易下这个判断,因此,就开始了“囫囵吞枣”式的接触艺术。比如,观察身边的朋友谁最会因为艺术产生热情,就跟着她去看一些展览,在看的过程中,观察她是如何欣赏这些我看不懂的画作和雕塑品。再比如,搜网上评分高的话剧观剧指南,找到近期在上演的就去看,结果,第一次看话剧就被台湾表演工作坊的《宝岛一村》中宏大的故事性和表演的细腻、贴心的剧场服务(如在表演结束后给每位观众发一份剧中老奶奶做的包子)感动了,接着,就像追电视连续剧一样一部一部地追着经典话剧,有些话剧甚至愿意花大笔开销坐到第一排去感受与演员、舞台的零距离接触,只为看清楚演员在表演时丰富的面部表情、妆容、服饰材质、手势动作以及舞台的布景。1-2年下来,以周均1-2个艺术活动的频率在来者不拒地接触着话剧、舞剧、默剧、油画展、网红展、装置艺术展、音乐会、音乐剧、电影等形式的艺术活动。这样密集的艺术活动,让我在不断的新鲜信息刺激下,逐步形成了我自己的“审美选择”,比如,我对“历史性严肃体裁的、名家导演”的传统话剧比较感兴趣,对大剧场的现场表演感兴趣,对古典音乐会感兴趣,对能够反复回味琢磨的表演感兴趣,对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反复琢磨及精进舞台艺术的老艺术家们“匠人般”的纯粹感兴趣……而这些看似零碎的、无关联的艺术刺激,对于我最开始思考的工作困惑的助益是什么呢?我想是给到了我更多的底气去思考和分享自己的教育期待。我开始有兴趣认真阅读机构给孩子们编写的艺术课程教材,对简单的艺术活动背后的“人文教育”有了更深的期待;而在对外的演讲、沟通中,我与他人的沟通语料,也不仅仅是自己小时候学习钢琴这样的简单故事了,而是有更丰富的艺术见解和体验分享,自己也显得更自信一些了。
另一次发生在2020年的4月下旬,因为工作上的需要重新梳理项目逻辑,大量阅读了国内外艺术教育的发展资料,以及,还研读了国内、国外的艺术史的发展历程,追根溯源地去看不同时期的艺术的功能性、艺术家的状态、公众对于艺术的需求状态。虽然,以目前自己肤浅的认识,艺术在不同的阶段,它有着不同的功能性作用,比如,宗教祭祀,表现上帝无所不在或为自己的狩猎活动祈福;标榜身份地位,展现家族的声望和品味;传递人文观念,记录地域风俗文化等;物品装饰,增强购买力;统治阶层对于民众的精神教化等等,但它在本质上还是在满足人类某种精神需求,以及在观看、聆听、触摸等调动多维感知功能后的一个综合式的体验,而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承载着创作者充沛的情感和表达诉求——“希望让别人知道,他们关心什么、信仰什么”。比如,在北宋绘画中,画家们喜欢用青山绿水来描绘大山大河的蓬勃生机,比如,在哥特式教堂建筑中,建筑师们希望借助彩色玻璃窗,让倾泻而下的阳光化作一缕缕彩虹般的色彩,让每一个走进教堂的穷苦信众即使无法理解玻璃窗上图像上的所有讯息,也能知道自己在体验某种神圣庄严的东西……这些,或许就是艺术的魅力,让人类可以通过更丰富的维度和视角去向外观察世界,向内探索自我,在创造性的探索中获得美的体验和内心的自我和解。而这于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自己在这样的寻找中,自我觉察变得性格上变得更加开放和敏感,走在路上不会再“视而不见”,会留意走道旁树木树叶颜色的变化,在听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四季》时也能带入更丰富的画面想象,而自己也逐步解开了自己2年前工作上的困惑——“艺术可以给人以滋养”,更加坚定它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上的意义和价值——让人回归本真,成为更纯粹的人;另一方面,对小学音乐、美术教育多了几分敬畏。原来那些看上去“无聊”、“枯燥”的民族音乐、手工背后,其实隐约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只不过自己还没找到合适的视角欣赏、品玩这背后的“美”而已。
反观自己在艺术上的后知后觉,我并不抱怨自己出身在小县城没有丰富的资源、没有好的引导老师而让我在艺术感受上多走了很多弯路,而是会觉得有点遗憾和可惜,可能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都在这样的成长境遇中对艺术产生了偏见,甚至对于艺术背后的文化也更加麻木。我不知道是否现代社会还可以回到当初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人对艺术有期待”的阶段,但现在在音画梦想这样一家儿童艺术公益教育机构任职的我,可能可以为今天的孩子、曾经的我做点什么。或许,只是通过艺术为孩子打开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又或许,只是让孩子在丰富多元的刺激后形成自己的主动判断,不会因为生长环境不佳而对自己、对环境形成单一的偏见。艺术于他们而言,可能终其一生只是个“无用”的爱好,但有这样一个了解外在世界和内在自我的窗口,自己一辈子的生活即使平淡但也有滋有味。
这,就是我在音画梦想的成长以及对“好的艺术教育”的期待。
附:新华网报道:青年公益说:初心不忘 “益”路不孤单